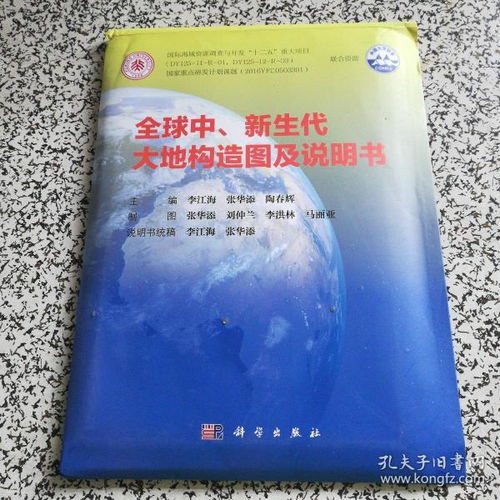在中国古代文化中,猫始终占据着一席风雅之位。南宋诗人陆游曾以“裹盐迎得小狸奴”描绘迎猫入户的仪式感,又以“尽护山房万卷书”道出猫咪守护书斋的文人雅趣。这般诗意的描摹,正是猫咪与风雅之事交织的绝佳写照。
古人迎猫讲究仪轨,据《礼记》载“迎猫为其食田鼠也”,而文人雅士更将此事诗化。陆游诗中的“裹盐”源自民间习俗——以盐为聘礼,郑重其事地迎请猫咪归家。这般仪式,既是对生灵的尊重,亦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。当小狸奴踱步于青砖黛瓦间,俯仰于翰墨缥缃侧,便为书斋平添了三分灵动七分禅意。
猫咪护书之说,实则兼具实用与象征。古籍易遭鼠啮,狸奴捕鼠天性恰成天然守护。然更深层处,猫咪卧守书卷的姿态,暗合文人“闹中取静”的处世哲学。明代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特设“猫窝”条目,主张“设猫窝于书房左近”,正是将猫咪纳入书斋雅器体系。那蜷缩于砚台旁的毛团,仿佛在提醒世人:真正的风雅,在于与万物共生的从容。
历代文人多与猫结缘。黄庭坚曾叹“秋来鼠辈欺猫死”,白居易亦写“狸奴护我寒窗下”,至清代《猫苑》更集录百则猫事。这些文字中的猫咪,时而是夜读时的温暖陪伴,时而是茶烟袅袅间的静观者,甚至成为画家笔下的水墨主角——沈周《狸奴图》中那回眸的灵猫,与案头瓶梅相映成趣。
当今时人养猫,虽少裹盐旧俗,却延续着与猫共处的风雅。在窗明几净的居室内,观猫嬉戏于书架之间,听其呼噜伴翻书之声,何尝不是现代版的“山房护书”?当我们为猫咪置备雅致的食器、编织精巧的窝垫,其实仍在践行着古人“格物致知”的生活美学。
小狸奴从古至今跃然于文人笔端,不仅因它捕鼠护书的实用,更因它身上那份不受拘束的灵性。正如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所言“猫的世界没有世俗”,这种超然物外的气质,恰是风雅精神的本质——在凡常生活中,守护一方精神的山水。当我们在键盘上敲打文字时,若有猫咪慵懒地卧于一旁,便是接续了千年未断的风雅弦歌。